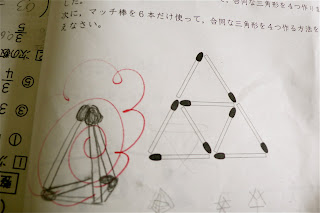很久以前,那时我刚到美国做生意。一天来了一位顾客,听介绍她给我的另一位顾客说,她是出生在美国的ABC,她在一家电视台做 播音员,会讲中文。那天她还没进门,我就听到 一个洪亮的嗓音从门外传来:“不好意思,I am late.” ,她那半中半英的腔调,我不用猜就知道她是何许人也,接着一位个头高高留着乌黑齐耳短发的年青女子出现在我眼前,她穿着一身西装套裙好一派豪爽女强人的风度。等我们相互打完招呼后,她又对我爽言爽语道:“对不起,我今天穿了太多的 Make-up 了。”“对不起,你穿多了什么?”我大惑不解地问道。她用手指了指脸说:“不好意思,我的中文不好,应该怎样说 I wear too much make up。”我恍然大悟,ABC的中文太逗了,她把英文直接译成中文了,我哈哈大笑道:“中文应该是这样说,化太多的妆了。”从此这件事成了我给朋友讲的一个有关ABC的经典笑话。

后来我又听到一则类似的笑话,它是这样讲的:一天彼得爸爸的朋友来找他爸爸,爸爸的朋友问:“你爸爸在家吗?”彼得是个很有礼貌的ABC孩子,他用中文回答道:“叔叔,我爸,走狗。”爸爸的朋友听了吓了一跳,心想,这孩子怎么这样说他爸爸,他瞪大眼睛说:“你在说什么呀?”彼得见状,知道自己回答的有问题,于是他这次用英文回答道:“My dad walks the dog.” 爸爸的朋友终于听明白了,他这才松了一口气,原来是这样啊。
打那起,我见到有人遛狗,我就故意学着这个ABC孩子的讲法,把他们统统称为“走狗”。但我没有想到自从我做了狗狗Pluto的“走狗”以后,我还挺喜欢的呢,我发现了许多“走狗”的乐趣,经常盼着狗狗Pluto来我家度假,这样我就有机会“走狗”了。



在美国住久了,越来越发现这里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,每个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,除了工作以外,一般很少有机会同别人打交道,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很少有机会去了解。每次离家出门,在车库里坐进车后就一口气开到目的地,不要说对沿路的地方从没有机会了解,甚至对自己住的邻里都是陌生的。
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有名的老区,还没有搬来此地时,就听人说这里环境好,街道优美,到处是有品味的住家建筑和情调浓郁的私家花园。看房子的时候,果然如其所说,我对周围的环境很满意,想象着住到这里以后可以经常在房子附近散散步,感受一下悠哉的乡村生活。




一转眼,搬进此屋都七年了,在没有“走狗”之前我对自己生活环境的了解几乎是零。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一个人在街上走,从来也没有见过有人在居民区闲逛,如果见到有人对着别人家的窗门有事无事地张望,那人不是被认为精神有病,就是心怀叵测的坏人,说不准还会被人打911报警呢。
美国人就是这样同咱们老中不同,他们绝对没有“远亲不如近邻”一说,对邻居的态度是,他看你时,未必是在同你打招呼,而你看他时,他一定认为你动机不良。所以就是开车经过邻居家门,我们都要目不斜视,绝不能放慢车速,窥视他人。

好奇心人人皆有之。其实,尽管邻里之间有点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感觉,但隔着窗门谁不在猜测彼此呢?如街对面的那家有三辆车的,老婆不上班,每天一早送孩子上学后,她的车就“派”在车道上;斜对门的那家先生好象是教书的还是自己做老板的,常常进出没有定时;还有我的左边邻居好象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活跃分子,每个月总有一二个星期五的晚上,他们家就有许多人来聚会,除了门口停了一大堆车外,他们家的厨房更是灯火通明。
我家的厨房有一个对着大街的Bay Window (海景窗,一种有宽平台的窗),我每天早上煮咖啡准备早餐的时候常会对着窗向街上张望一下,偶尔我会看到一些“走狗”的人停在我的前院,他们一边耐心地等待他们的狗专心地满地闻,一边两眼发直有看没看似地打量着周围,他们这种四周张望的行为绝不会引起他人的反感,因为他们有狗做伴。在这个狗的地位相当高的社会,狗想做的事,是绝对无可非议的。
狗狗是遇到树就要停下来闻,看到小灌木林必定要在上面撒尿。狗的这种人人皆知,但人人无知其果的行为,它们的主人为之不时止步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,所以一边“走狗”一边乘机察看周围就显得很自然。见此情形,我就好羡慕“走狗”,心想,如果我有一条狗就好了,我就可以无所顾忌象他们一样,正大光明地,大摇大摆地,边“走狗”,边对我的邻居来个调查。
我向来都有“心想事成”的好运气,一年半前,我的好朋友玛丽家养了一条叫Pluto的小狗,每当玛丽同先生外出旅行,我就自告奋勇地把Pluto接到家来替他们看护,因此我终于圆了借“走狗”了解我家周围情况的梦,现在我对我家方圆几条街的情况了如指掌,不瞒你说,我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“活地图”。
Paco街是一条两头被大路断掉的小路,我住在它靠西边的那头,每天出门我就右拐上大路,对东面的人家一无所知。自从Pluto来了,它一出门就喜欢向东跑,我这才有机会开始打量街上所有的人家。
我们这条街因为地形的关系都是小门面的房子,不长的街却有四五十家,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只有一车房,所以看上去都不是有气派的豪宅。街的右面的房子近几年来都翻修过,它们显的比较整齐,但还有一二家仍然破旧不堪,有一栋的车房门还是象农庄关牛马那样的半截的呢?那栋把以前的一口旧井改成信箱的老房子,去年总统大选时,在它的前院插满了支持Obama的标语牌,不知Pluto是哪个党的,每天它一走到这里,它一定会在那些标语牌前撒尿。一见此状,我心中窃喜,狗可以替主人示威却不会引来麻烦,这也是我意想不到的“走狗”的惊喜。
在Paco街上还分出三条小街,一条很短叫Roman,上面只有七八户人家,一条很长叫Clark,如果沿着它走可以走去很远,还有一条叫Silvia是一头到底的中文称“死胡同”、英文称“court”的街,有一些爱摆弄文化的人常称之为“Cul de Sac”。一般如不住在这个Cud de Sac的人是不会走进去的,开车的话就更不会随便闯入,因为在Court的街口,常常有一个很醒目的警告牌,上面写着 “ Not a through Street”(此路不通)。但我听人说Cud de Sac里的房子通常都比较漂亮

Pluto是一条小狗,它走不了太长的路,所以我常选那条Silvia 街走,然后沿着它走到Silvia Court , 到底以后就可以掉头打道回府了。

一天,我带着Pluto又走到Silvia Court,来了这里几次我已对这个Cud de Sac里的房子有所了解,正如人们所说,这里果然有漂亮的房子,特别是到底的那两家我尤其喜欢。右面的那家,房子不大,房子刷的是白色的石灰墙,有一扇黑色的Shutter (百叶窗),屋顶上有一个红砖烟囱,前院用黑色的铁篱笆围着,透过篱笆满园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玫瑰,尽管加州阳光充裕,玫瑰长得好不稀奇,但满园棵棵都如此健康的玫瑰依然少见。还不到盛夏,这家的玫瑰已开满了枝头,鲜艳得花朵攀着黑篱笆伸出头来,把房子装点得象童话故事里描述的英式小Cottage(农舍)一样。左边的人家是另一种风味,窗前是两棵红枫树,一块修剪得一丝不苟得绿草坪,没有种任何花,在右边的围墙边是清一色白玫瑰,我最欣赏它的地方是那一株爬满车库门的淡紫藤,它的花一串一串的低垂着,象是害羞的娇女含情脉脉地沉思着。这家的主人显然是爱静和喜欢优雅色调的那种有“品味”的小资。
对着这两家可爱的房子,我每次都特意让Pluto在它们门前多留一会,这样我就有理由对着它们多欣赏一会。这天无意中,我发现在两栋房子的中间有一条小路,那路之小除了人和狗可以走,大概只有一辆自行车可以通过。我对我的发现万分地惊喜,我牵着Pluto,小心地穿过小路,我突然发现我们来到了另一个Cul de Sac 的底。就象在“桃花源记”里那个渔人迷失了方向后,突然眼前一亮发现那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一样的欢喜, 我在惊喜之余开始打量起我的新发现来。
原来这个Cud de Sac 同我家街上那条最长的路Clark 街是通的,它叫Clark Court,如不是“走狗”我是无伦如何也不会想到它同Silvia Court 是背靠背而相通的两个Cul de Sac。
在Clark Court里我也发现两家很有意思的人家,一家是靠近Court的底部右手边的那个,它可以说是我在方圆几里发现的最特别的前院。它没有一点规划,也谈不上有什么形式,房主人完全是属于那种无拘无束,绝对任性型。除了车道,其他地方一眼望去,杂乱无章,每次路过我都想避免看它,但它却偏偏是Pluto的钟爱,我怎么拉它走开那里,它都坚持要去那转一转。无奈,我只好奉陪,谁叫我是它的“走狗”呢?
当我终于走近它,对着乱七八糟的院子细细打量,我诧异地发现,原来这是一个菜园子。里面种了黄瓜,扁豆,番茄,沙拉菜,更吃惊的是,我还发现有玉米。天呢,原来这家把菜园子种在大门口了,难怪这么乱呢。通常,大家都是把菜园子放在后院的角落,大胆把菜种在前院的是一家怎么样的人家呀?我好奇地把房子好好审视了一番,想找到答案。但我没有发现诸如门前有鞋子是中国人,窗帘用米色尼龙是印度人之类的蛛丝马迹来,几次经过都也没见到有人进出,至今仍是一个迷。

同这家非常奇怪的人家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路对面那家,它整整齐齐的草坪,错落有致的园林设计,小山石和小草被红木屑有模有样地围着,最动人的地方是大门前那随风飘扬的小旗子,一看就知道主人是收藏旗子的那类人,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挂不同的旗子, 以此来增加生活的情趣,如情人节,挂有红心的那种,万圣节挂有南瓜的那种,等等。看着他家的旗子,我们就会知道现在在过什么节或是什么季节了。
如此不同的两家人,他们每天遥遥相望着,我不知他们会怎么相互感受,从前院的形式,我们不难断定他们是绝不会苟同的那一类,我为他们要相互忍受深表同情。
自从发现Cul de Sac不一定是“死胡同”,我再也不受竖在街口黄色的“Not a through Street”标语的迷惑,我决定带着Pluto把我家周围所有的“死胡同”都走一遍,果然我们发现了无数的世外桃源,现在我可以屈指向人如数家珍那样介绍我家附近的住家情况,我可以告诉你哪家是我最爱的现代建筑,哪家有我最爱的Dogwood树,哪家有日本禅式花园,哪家有参天的竹林,哪家有艺术雕塑造型的信箱,哪家是新搬来的新贵,还有哪家是门前常常车水马龙最爱开Party的。对我这些从未见过面、打过招呼的邻居,他们全然不知我竟然对他们有如此的了解,奇怪中我不免有些得意,仿佛我感到我现在已有资格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“ Local”(本地人)。


对“走狗”我是越走越来劲,越走越有滋味,越走越有看头。如果几个月不“走狗”我就会想念这些对我一无所知的邻居,我在想,不知那家的菜园子又种上了什么菜?那家门前又换什么旗子了?那家英国农庄的玫瑰又开了什么颜色的花?那家正在翻建的房子不知完工了没有?
我对我这些“陌生”的邻居的关心常使我感到温馨,在这缺乏人情味的地方,没想到“走狗”给我带来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情感,原来爱也可以这样产生的。如果你也想了解你的居住区,你也想关心你的邻里,你不妨也来养一只狗,或向朋友借一条狗,或象我一样在朋友远行时替他们看狗,这样,你也可以来“走狗”,以此来关怀你的邻居们,你一定也会成为你家附近的“活地图”。